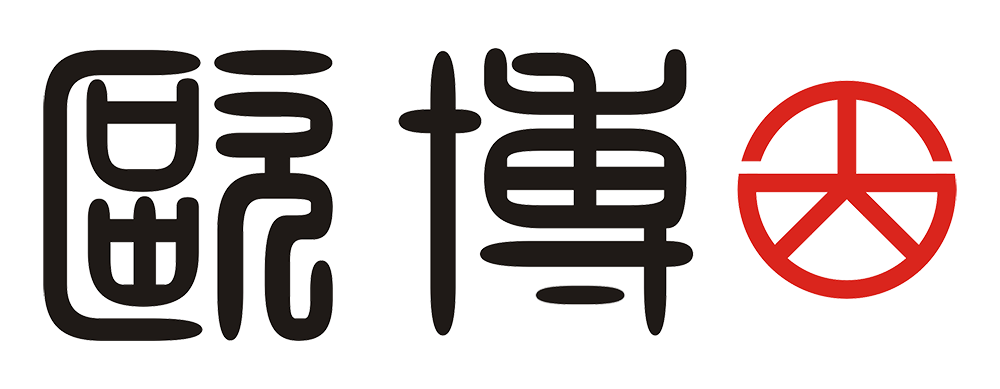儒家辩证法与马克思自由观
作者:曾伟
一、真假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体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更是主体中的“主流”,因为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政治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成为了社会的统治思想,无论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何为儒家以及儒家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而这其中又以传统文化爱好者最为自信,仿佛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对儒家思想自然了然于胸,何为儒家?还用问吗?当然是孔孟之道了,但何为孔孟之道呢?《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不是讲的清清楚楚的吗?这有什么疑问呢?看不懂这“四书”或未看过“四书”可能不懂儒家,但认真研读过“四书”的人怎能不懂儒家呢?这就是很多崇尚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对待儒家的心态。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人对儒家的了解并不是源于对“四书”的钻研,而是在生活中受儒家思想的耳濡目染的影响,从而了解了儒家,因为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渗透传承,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中,很多都成了民间的口头禅,哪怕没读过多少书,没上过几天学的人也都对儒家思想并不陌生。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传承至今的现状:仿佛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能说。但事实的真相如何呢?从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直至黑格尔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批判否定,以及上个世纪初暴发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我们不难看到儒家思想在近现代所受到的由外而内的强烈冲击,这是为何?是儒家思想错了?还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错了?还是儒家思想的传承错了?这里是否存在真假两个“儒家”?真正含在“四书”中的孔孟之道,与通过历代帝王及其文化体制,以及依附其上的卫道士们所过滤了的“孔孟之道”,是否并不一致?以至于时至今日所呈现的并非真正的儒家,而是完全政治化了的被历代文化人所扭曲了的“儒家”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西方思想家的批评便很好理解,因而也上升不到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来看待这些批判和否定了,相反,正本清源或许还能找回真正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就是本文的初衷。
谈“孔孟之道”当然要从孔子谈起,但如果对“四书”的了解就从《论语》开始,那就找不到真正的源头,这就是很多古今中外儒生“死读书,读死书”的陷阱。因为孔子的思想从何而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儒家思想的源头。对了!《易经》才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同时它也是道家思想的源头。根据何在?孔子五十多岁解《易经》,而这恰恰是他自己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之时,这是巧合吗?不是!是孔子从《易经》当中获得了对世界、社会、人生大彻大悟的认知和了解,也可以说是孔子达到了对世界、社会、人生大彻大悟的认知和了解才能真正解读了《易经》,总之,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孔子对《易经》的解读仍是今日学习《易经》之人必须学习和依靠的读本。孔子解《易》是儒家思想形成的关键节点,所以,了解儒家思想必须追到《易经》上去,由此也才能理解道家思想,以及儒、道两家的相通和不同之处。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辩证法”思想。但这并不是“思辩”的“辩证法”,或“思维”的“辩证法”,而是“生灭”的“辩证法”。中国的儒道两家的后世弟子们为何在《易经》的解读上难以突破,最后玩成了文字游戏,语言游戏,就是因为很多后人落入了“思辩”陷阱不能自知和自拨,从而不仅毫无建树,还阻碍了真正《易经》思想的传承和传播,以至于到了西方的黑格尔这里,这一以“生灭”为本的“辩证法”思想才得到了纯哲学式表达,以此影响了人类近现代思想史和文明史,这才是做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传承者最大的悲哀!
关于“辩证法”作为“生灭法”与“思辩术”的区别,我在《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交叉性思考》一文中已有较多探讨,此处不从理论上来进行比较,我们先看看孔子《论语》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首先,孔子在对于“理想人格”的阐述中始终秉承的就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君子与小人。读过《论语》的人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比对性语言一定印象深刻,这里不一一举例。为何孔子会采取大量的比对式的语言来阐述他所倡导的理想性人格“君子人格”呢?因为他深知“君子人格”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孤立的“君子”是不存在的,他只是“小人”的否定和超越,可以说,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众生”、“常人”,这也恰恰就是孔子讲的“小人”,是指心量格局不能超越自我,一切从“自我”出发的人,这种人是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活得并没有错,尽管自私狭隘,但只要不伤害别人,又何错之有?看看《论语》中的关于“小人”的论述是不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小人”活错了,而是如果你想在社会上有所建树和成就,你该怎么办呢?很简单,由“小”变“大”,正如孔子的弟子曾子在《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谓“大学之道”?即成为“大人”的学问和方法。“大人”是相对于“小人”而言,即超越“自我”,能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人。“小人”是仅对自己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当然没错,现如今如果人人做到对自己负责这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这还不够,我们组成一个社会、一个组织,还需要为组织为社会负责的人,这种人是需要有超越自我的境界和胸怀的,这就是心胸有大格局的人,简称“大人”,也叫“君子”。这就是孔子“君子”人格的由来。
我们谈了“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和否定,那又何为“君子”与“小人”的统一呢?只有“对立”没有“统一”就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这里恰恰是我们理解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岔路口,很多人就把“君子”视为“小人”绝对的对立面,把“小人”视为可耻的道德上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格,而把“君子”视为高尚的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格,这是不懂孔子的“辩证思想”所致,在后世的帝王、文化人的共同推波助澜下,这一两极对立的人格理论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君子”因为人格完美无需制约的青天老爷文化,而“小人”因为人格缺陷无权干政的刁民文化,由此中国人的人格开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最终绝大多数人因为是“小人”人格而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而成为了“君子”人格的奴仆,成为了西方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以及我们新文化运动所批判和否定的失去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的“礼教”文化。其实这一事件的分水岭发生在对“君子”与“小人”之对立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还是绝对的否定?那么,何为“辩证”的否定呢?
要理解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辩证”思维,就要理解儒家文化中的“圣贤”思想,也就是说,“君子”其实并不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是“圣贤”,何为“圣贤”呢?因为孔子在《论语》中大量的篇幅谈论“君子”,甚至孔子都自认为自己能成为“君子”已经很不错了,将“君子”视为现实的“理想人格”,极少谈到“圣贤”,所以,我们借助佛家的眼光来看看何为“圣贤”?《金刚经》言:“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圣贤”是活在“无为法”这个层面的人,那么,显然,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活在“有为法”这个层面的。何为“有为法”呢?《金刚经》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所以,“有为法”指的就是我们的“现象界”,也就是所谓的世俗的世界,通俗的说就是“现实”的世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格,是现实的“两极”,尽管彼此对立,但也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君子”有君子的意义,“小人”有小人的价值,他们彼此并不是绝对否定和消灭关系,而是相互依存,超越自我的关系。“小人”需要超越自我,以适应社会需要,“君子”也要超越自我,不要鄙视小人,引领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本质上“君子”和“小人”还在一个维度,都在“有”的层面,正如同“生”与“死”在一个维度一样,都在“有”的层面,所以,常人看不破“生死”,因为我们都活在“有”中。只有“圣贤”才活在“无为法”中,他们既不属于“小人”,又不跟“小人”对立,也不属于“君子”,不跟“君子”对立,只有“圣贤”才超越了“对立思维”,他们觉得“小人”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正是芸芸众生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邓小平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普通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和价值,带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我们当然可以批评社会变得自私了,但没有社会对“私有”观念的肯定和重视,私有私营企业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就业如何解决?所以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是站在“公有”角度肯定“私有”的人,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君子”的视角,而是能超越“公、私”对立来看待“私有”的眼光,是超越“对立”看到了“对立”背后的“统一”的眼光,这是“圣”者的眼光,这就是“辩证法”的眼光,由此带来了中国历史性的复兴。
“圣贤”当然也会肯定“君子”,促使“小人”超越自我向“君子”学习,使社会一体。所以,“圣贤”对“小人”是肯定的,对“君子”也是肯定的,因为对“小人”的肯定,从而调动了社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主意识,让社会充满活力。而因为“圣贤”对“君子”的肯定,自然就拥有了对“小人”否定的一面,拥有了促使“小人”超越自我的一面,拥有了肯定“私有”但却引导“公有”的一面。而他对“君子”同样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因为“君子”作为“小人”的对立面容易看到“小人”的缺陷和不足,而不容易看到“小人”积极的有价值的一面,不容易看到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提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无穷动力。“君子”们看到了“小人”的自私,所以他们不遗余力的引导“小人”们一心向公,而挫伤和抑制了“小人”们自私自利倾向的同时,往往也就挫伤了深深根植于个体身上的社会创造力,结果适得其反,这就是“圣贤”既肯定“君子”又否定“君子”的原因,否定的目的是让“君子”们也不要执着于一己之见,而真正懂得引导和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之,在“圣贤”这里,事物总是“肯定”和“否定”集于一身的。“肯定”就是“否定”,“否定”就是“肯定”。最终超越“肯定”与“否定”,不在“肯定”与“否定”这个层面,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这就是“辩证法”的哲学表述。而从儒家来讲,“小人”、“君子”、“圣贤”也恰好形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层阶梯,当然,第三层的“圣贤”就如“否定之否定”一样,并不在前二者的对立当中,前二者是对立的两极,都在“有”这个维度,第三层超越“有”的维度,进入“无”的境界。
刚才是从儒家的三重人格上谈了儒家的“辩证法”思想,其实在儒家的具体修法上也充满了“辩证法”思想,这一点读懂了曾子《大学》的第一句就会一目了然。《大学》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修行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明明德”,第二层“亲民”,第三层“止于至善”。也刚好构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模式。“明明德”就是“明良知”,也就是明白每个人自身“良知”的存在,这一层的明白还是概念上的,佛门叫“知见”上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道理”上的,也就是我们道理上明白了相信了人人皆有“良知”,这叫“明明德”。是对“良知”的第一层“肯定”。但这样就够了吗?这种人真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是过不去坎的,烦恼、瞋恨、恐惧、担忧照常生起,自己的“良知”毫不起用。所以,必须进入第二层“亲民”,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真心与人去打交道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个修行人会屡屡受挫,让你直接看到数不尽的无良之人和无良之事,这是对第一层概念上道理上明白了良知存在的“否定”,叫“亲民”。为何要叫“亲民”呢?因为这些无良的挫折感只有你满心“亲民”的过程中才能感受得到并且感受强烈。很多人在这个环节就“牺牲”掉了,而只有极少数不改初衷的人才能穿过这一“无良区”,走到第三层次。能穿过“亲民”这一“无良区”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自我批判、自我觉知,看到自己的问题,一点一滴的修正自己,这就是儒家讲的“克己”,这也就是《大学》后面讲的“诚意”的功夫。无尽的“亲民”,无尽的“克己”,无尽的“诚意”之后,若还能坚持初心,坚信“良知”,就完成了“否定”当中的超越。因为“坚持”,因为“坚信”,而从“死亡中得以自存”,“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黑格尔语),这就叫“否定之否定”。到达了超越“肯定”和“否定”的境界,即到达了超越“生”与“死”的境界,到达了“非善”、“非恶”的境界,也就是“至善”的境界,进入第三层:止于至善。这就是儒家修行的“辩证法”。
二、马克思自由观。
“自由”几乎是每个人都喜欢谈论的概念,那句关于“自由”的诗更是很多中国的文化人喜欢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在很多人的心中,“自由”是高于一切的价值,甚至高于生命和爱情。那究竟何为“自由”呢?关于“自由”的“辩证法”又是怎样的呢?
谈到“自由”,很多人都把它当成“约束”的对立面,认为不受约束就是“自由”,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自由观”是“自由”的第一个层次,即对“自由”的直接“肯定”的阶段,但很显然,这不可能是“自由”的终极意义,因为秉持这种“自由观”的人,在生活以及社会中是会处处碰壁的,因为一个不愿受约束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受欢迎的,因为他不受规矩,而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这样的人在组织中就是破坏因素,所以,他必定会受到组织的排斥而一事无成。其次持有这种“自由观”的人也往往非常的任性和随意,他们很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活得障碍重重。所以,如果说“自由”就是不受约束,那么,事情立马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不自由。这就是“自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不自由”,这是对“自由”的“否定”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体现为那些“任性”人的处处碰壁,也可以体现为社会、组织、他人对“任性”者的教训、束缚、惩罚、阻碍等等,总之,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你一直追求“自由”,你所追求的“自由”就必将进入到第二阶段:否定阶段。而在第二阶段中人有两种选择:逃避约束或重新认识“自由”。逃避约束追求“自由”的人这一生一定活在无休止的逃避当中,既一事无成,又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是处在“不受约束”的囧困状态。而重新认识“自由”的人才可能进入“自由”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何为“自由”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呢?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自由观”。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从人的本质的思索出发而形成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包含了三个层次:生命活动,有意识,自由。“生命活动”是人与一切动物乃至植物的共同点,这是人至为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有意识”的活动这也不仅仅是人的特征,许多动物也有“意识活动”的特征,所以,至少不要将人的“自由”定义成“随意”,因为这对于许多动物而言都不稀奇,当然人的这层含义又比普通生物的含义进了一步。最后成为人的本质特征的就是“自由”了,所以,“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那何为“自由”呢?在马克思这里,“自由”是与“普遍”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说: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也就是说,人的“自由性”来自于人的“普遍性”,而何为人的“普遍性”呢?马克思说:“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3。显然,马克思认为人的“普遍性”就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自然界既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的无机界”,又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无机的身体”。所以,所谓的“自由”不是一个人的为所欲为,而是人与万物的普遍联系,以及在这种普遍联系中的浑然一体,和谐自在。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和谐自在”的,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孔子“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就是这样的境界吗?康德的“道德人”理想----个人行为准则与普遍立法的统一,表达的不也是这样的境界吗?所以,“自由”的第三个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就是“约束”和“自在”完全统一乃至合一的阶段:“相”上有约束,“体”上很自在。“相”上的约束表明人与万事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这叫“一即一切”,“体”上的自在代表人与外界达到了和谐相通,这叫“一切即一”。
正因为马克思是将人的本质以及“自由”都是从人的“普遍性”及“普遍联系”出发来看待的,所以才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我们所熟知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用简洁明了的一句话来概括了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5。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6。这就是马克思的“自由观”。
三、儒家辩证法与马克思自由观。
儒家的核心理念是“仁”,何为“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所以,“仁”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克己”。为何要“克己”?如果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或第一个层面:不受约束。那么显然,“克己”的思想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因而,儒家的核心理念“仁”也是与现代观念“自由”相矛盾的,这可能就是现代很多人包括西方哲学家普遍否定儒家价值观的原因。因为“自由”已经成了现代人的普世价值观,而与“自由”相对立的价值观当然要遭到人们普遍的否定,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问题在于,依辩证法的观点,“自由”的价值观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普通人直观的理解,它是与“约束”相对的价值。但这其实并不是“自由”的本质内涵,“自由”的本质内涵是超越“约束”和“反约束”的二元对立的,是马克思讲的“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自由”,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自由”与“共同体”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失去了“共同体”,个人就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人失去了自身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生存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自由”。正如同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或名牌大学毕业就不太好找工作一样,他因为没有成为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那一类人,就失去了找到好职业的“自由”。所谓的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那一类人”,其实就是某一个“共同体”而已,可见,事实上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你就失去了很多机会,也就是“自由”,在这些生存和发展的“自由”面前,一个人独来独往的“自由”显得毫无意义和价值。现在演艺界的“圈”,企业界的“圈”,不都证明了“共同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吗?要不然人们还努力的混“圈”干嘛?只不过这样的圈子太小,我们要从这样的小圈子扩展到家国天下的大圈子,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
儒家经典《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讲“克己”的最终目的就是达成这样的“共同体”,而“克己”的过程和方式就是“修、齐、治、平”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只有站在“自由”的第三层境界,即“否定之否定”的超越境界,才能明白“克己”是形成“共同体”,进入“共同体”的前提,从而也就是获得真正“自由”的前提和途径,才能明白“克己”就是“自由”,“自由”必须“克己”。这就是“自由”的辩证法,也就是“克己”的辩证法,这才是儒家精神的要害之处。
当然,如果“克己”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从个人的“意志”出发,或者是从社会的“教化”角度出发,而是成为一种社会强制,这当然是对“自由”的背叛,对人性的摧残。正如同一个人有加入一个组织的自由,也有不加入某个组织的自由一样,人可以融入社会,也可离群独处,所以,将“自由”与人的“共同体”相连,只是客观规律的揭示和对人善意的教导,是文化的教化而非制度的强制,这就是儒家精神与后来被帝王们推为封建礼教的区别。圣人们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告诉世人,他们并没有强求人们怎样,一切都靠人们自己的感悟和选择,所以,圣人的心是随缘的,随顺众生的,决不强求的。所以无论中国的儒释道或者西方的哲学思想,都是教化众生的精神食粮,而绝非强制百姓的制度法规,是人们可以接受选择,也可以另行选择的,只不过生活及历史会让人自己醒悟从而最终选择它,背离它的人受到生活的磨难,有的人终生未醒,圣人们也是不加惩罚的,因为生活与命运已经惩罚了这些人,圣人们对此除了悲悯,还能怎样呢?而有的人终究觉悟,这叫回头是岸,圣人们当然欢喜。但无论怎样,圣人们是将选择权给到众生的,这就是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圣人们是绝对尊重的,正如同人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一样,所以,任何一种圣人的文化都绝不与“自由”对立。对立的只能是后来那些利用圣人的文化管理众生的人,这又与圣人何干呢?所以,做为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和作为管理之道的儒家文化不可等同,后者是历代君王及卫道士们的作品,是不崇尚“自由”的,无论遭到现代谁的批判都理所应当,而且绝掩盖不了真正儒家精神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域的大放光彩,这才是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的根据所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9页。